看領導面子評!高校教學成果獎,怎么變了味
“像這樣前沿的改革,你們又不是院長、校長,怎么可能有能力去談創新?”在東部某高校的教學成果獎申報中,評委一番“獨到的見解”,讓前來答辯的基層教師怏怏而歸。
近日,不少高校、省市啟動教學成果獎申報工作。“其中,教學成果獎由校領導掛帥、生拼硬湊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在‘雙一流’、學科評估中加大了教學成果獎權重的背景下,這種現象已達到了白熱化。”該校教授張毅(化名)說,為了獲獎,一些沒有做實質性貢獻的校領導成了第一完成人,而實際貢獻者被擠到了靠后的名次,更有甚者被挪出了申報名單。這讓在一線辛勤探索教改多年的教師感到無比失落與沮喪。
獲獎的機會讓給了更有贏面的人
“前沿改革只有領導做才無可厚非,基層教師做就要備受質疑。”在張毅看來,這一聽起來荒謬的邏輯,背后的潛臺詞是,“把教學改革的成果留下,但把爭取獲獎的機會讓給更有贏面的人”。
誰是更有贏面的人,顯然在前述答辯中已有答案。
《中國科學報》記者查看了東部某高校教學成果獎申報名單,十幾個校內特等獎中,由校領導掛帥的項目占了70%。校長、副校長的名字分布在若干個零敲碎打的項目中,甚至部分項目的前幾名完成者,均為校長、副校長。
只是,校領導真的有實際參與嗎?
一些基層教師忍不住向《中國科學報》吐槽,部分校領導甚至連一節課都沒有上過,就成為了項目的第一完成人;有些校領導近年才剛剛調任至學校,就被安上了歷時多年教改的完成人。
而很多高校在更高級別的獎項認定上,只認前10名或前5名完成人,校領導紛紛“插隊”,導致實際貢獻者卻成了“無名英雄”。
甚至還有高校要求教師放棄或退出自己的教學成果申報,把該成果歸為學校所有,以便再二次“發揮”。
在另一份東部某高校公示的教學成果獎推薦申報名單中,記者看到“成果主要完成人姓名”一欄,部分項目公然寫著“學校項目”,且沒有申報者人員名單。“此舉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給暗箱操作提供了各種可能,也違反了公示的原則。”張毅指出。
不只是校領導掛帥的問題,“報獎過程中,你會發現很多教改成果,只是人為地拼湊或攢一些概念”。
山西某高校教師李想(化名)舉例,如在申請教學成果獎時,五花八門的獎項都會被打包進來,“尤其是創業類的獎項更像是‘萬金油’,哪個類型獎項申報時幾乎都可以沾邊”。當中,不乏從前已經獲獎的項目,再經加工“改頭換面”繼續申報。
張毅也有同感。“如今的教學成果獎不再是對一線教師在教育教學改革與實踐中所取得的成果獎勵,而是異化為校領導分管工作的成績表征。”他舉例說,如很多高校申報的項目基本上都是“XXX 教育改革的探索與實踐”“XXX 人才培養質量體系的構建與實踐”……不禁讓人質疑,所評的究竟是教學成果獎,還是教學管理成果獎、“校領導領導有方”獎?
“學術生態”變成“報獎生態”
為什么會出現這些名不副實的報獎?
背后的邏輯并不復雜。教學成果獎是對一所高校教學改革成績的肯定,“對其申報已成為一些高校的戰略行為,舉全校之力操辦,導致‘學術生態’變成了‘報獎生態’。”李想說。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一般高校會提前一年或更長的時間先內部篩選,篩出之后對獎項做“重點培育”,給予經費、資源等各方面支持,其目的是爭取更高層次的獎項。“最終的結果是誰的經濟條件好、做了組織工作,誰就更容易獲獎。”
由校領導掛帥報獎,通常出于兩種情況。
儲朝暉解釋道,一種情況是,校領導牽頭,方便調度各種資源。比如要鼓勵課題組之外的教師、學生參與,只靠基層教師很難調動,以校領導的名義,更有利于項目的順利推進。
另一種情況則是,申報時臨時掛名。很多時候,校領導的初衷并不是為了自己拿獎,而是為了讓本校項目獲獎。這對于提高高校的辦學聲望、校領導的辦學政績而言,很有顯示度。
反之,沒有校領導參與,在申報時可能第一二輪就會被刷下來。
看校領導的面子評獎,已成為報獎生態中的風氣。“越是基層的評獎,校領導面子越能發揮作用。有的評獎中甚至拿出一張空白的表格,讓評委在上面簽字、打鉤即可。”曾做過教學成果獎申報評委的張毅無奈地搖了搖頭。
在這種情況下,也就無怪乎寫作班底為了配合校領導掛名或將從前的獎項“改頭換面”后申報,將項目包裝得大而虛。
不過,這些“擴容”細究起來經不住推敲。張毅指出,很多內容都是校領導分管的本職工作,是其職責所在、理應做好,做不好要追究責任,而現在卻演變成了領導表功的成果。
“可是由于評選過程中的工作量非常大,評委們很難一一發現問題,也沒有發現問題的機會——因為核對起來需要做大量的功課。”李想說。
讓教學成果獎回到一線教師手中
事實上,早在2018年下發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關于做好2018年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推薦工作的通知》中,就已明確要求,“在推薦過程中,現任學校領導牽頭成果的推薦數量應控制在推薦限額的30%以內”。
但據《中國教育報》統計,當年獲獎的452項成果中,第一完成人為校領導的仍有187項,占獲獎總數的41.37%。
張毅指出,要嚴格限定校領導申報數量,“這個比例應從30%降至15%及以下,讓辛勤耕耘在一線的教師的創造性得到充分肯定與表彰,因為真正能夠產生教改成效的是一線教師”。
儲朝暉補充道,得獎比例應參考該校領導與一線教師比例,比如一所高校的校領導只占5%,那么校領導得獎的比例理應控制在5%及以內。
在他看來,讓評價回到原生態,有三個方案。第一,取消教學成果獎評比,采用美國教育家科爾曼的增值法評價,依教學效果評價教學成果;第二,考慮到直接的利害關系,改變目前由教育主管部門評價的方式,將評價權力交給第三方機構;第三,各地建立規范的監督與舉報機制。
在李想看來,教學成果獎對于推動高校重視教改,起著重要作用,當下取消該獎項評比并不是高校所樂見的。
張毅對第三個方案表示認同。他建議,在目前教學成果獎申報改革尚未啟動的情況下,應嚴查申報中獲獎內容真偽、知識產權侵犯,及從前申報并獲獎卻又改頭換面繼續申報的項目等問題,對于嚴重敗壞師德師風的問題,應實施一票否決制等措施。
對于存在問題的申報事項,要對相關項目與人員進行追責,并取消下一屆申報資格;甚至于請紀檢委參與監督整個申報過程,設立舉報機制,如此才能還教學成果獎申報與評審一個風清氣正的環境。
-
標準

-
政策法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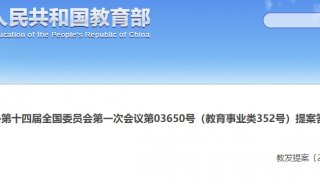
-
項目成果

-
焦點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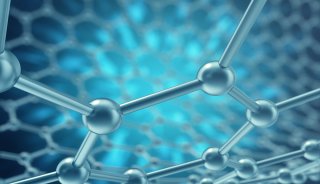
-
焦點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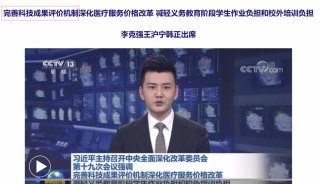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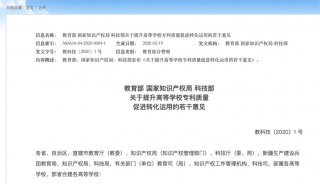
-
焦點事件












